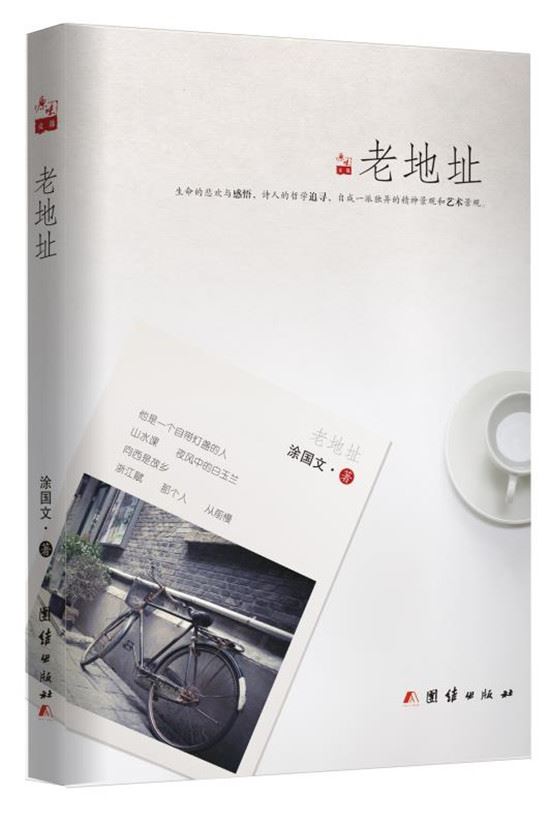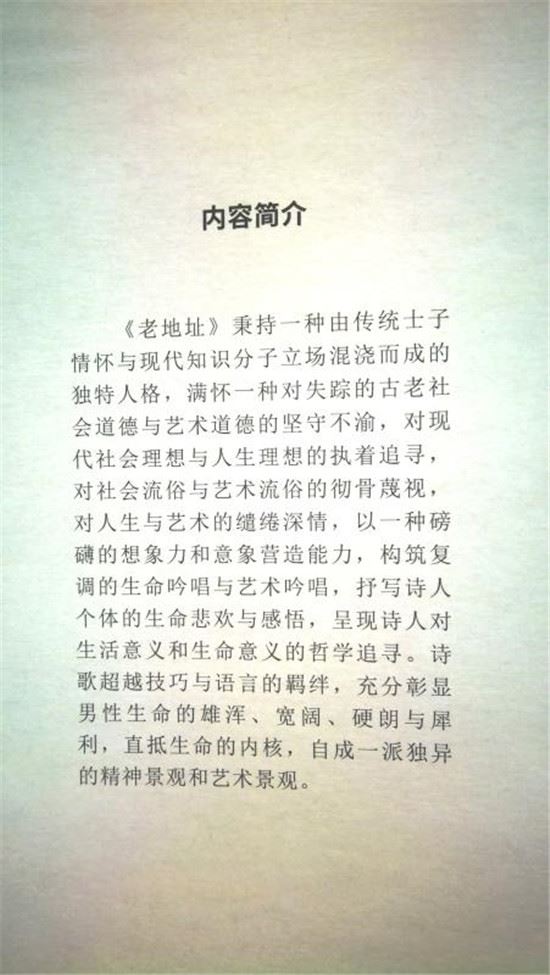文/王克楠
笔者与涂国文是十几年之前由一部书而认识的,那部书是他的一部随笔集,很厚,书名印象是《苏小墓前人如织》,那个时候只是知道他的散文以及评论写得很好,并不知道他还擅长写诗歌。可以说,国文在对文学体裁的操作方面,是一位全面手,由于才华所在,对于各种文体驾驭得游刃有余,有文学评论集《词语快跑》,有长篇小说《李叔同情传》《苏曼殊情传》等。
著名诗人俞强说:“涂国文的诗歌将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江南气质,将唯美抒情与思考淋漓尽致地糅合于那喀索斯的自我情结中。”而在笔者读来,涂国文的诗歌更是白描的,是不事装饰的,是在不经意中触摸到了世界的本质。比如《搬动一把椅子》,虽然仅仅是一种物体的移动,作者却在不经意中感到“便会发生大陆漂移”,诗人写的世界上的事情,或大或小,都有“相似之处”。诗人还联系到王安石变法,联系到林肯废除了北美的农奴制,这就更加强化了内在“漂移”。再比如诗歌《石头》,石头本来是一种固体的物质,诗人却赋予它新的生命,“石头更愿意跟随流水走”,诗人把流水与石头互相进行映照,强化了人类想象力。再比如诗歌《散步记》本来是人的一种日常活动,但作者却放大到了运河的散步、大海的散步等。各种不同的“散步”当然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景象。
诗人一生都在忙碌。都在寻找写别人所未写的突破口,但是到底哪些是别人所未写的呢,有的时候不妨退一步。别人写过的没有关系,你换一个角度,换一个常人不注意的角度,一个更加人性化的角度去写,说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呢。现代诗歌到底是“再现”,还是“再创”,涂国文有着自己的诗歌美学,他对城市生活进行观照,把城市人比作城市鼹鼠,这并非是信马由缰的想象,而是源自他对城市生活异化的观察与理解。诗歌《招领启事》从表面上看是写实的,实际上是整体象征,是对城市人心灵走向的梳理,“那些面具,却带着灿烂的笑容”这是对于城市万花筒的五彩缤纷深刻的洞察,其中对“塑料手掌”描写更是这样,当人的肌体可以用塑料代替时,人生将会变成什么模样?更不要说很多人以“假心”生活,实在令人毛骨悚然。生活中有悲剧,所谓悲剧,是把美丽的人生砸碎给人看,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诗歌在表现生活时,砸碎了外表碎片,飞溅出的本质碎片越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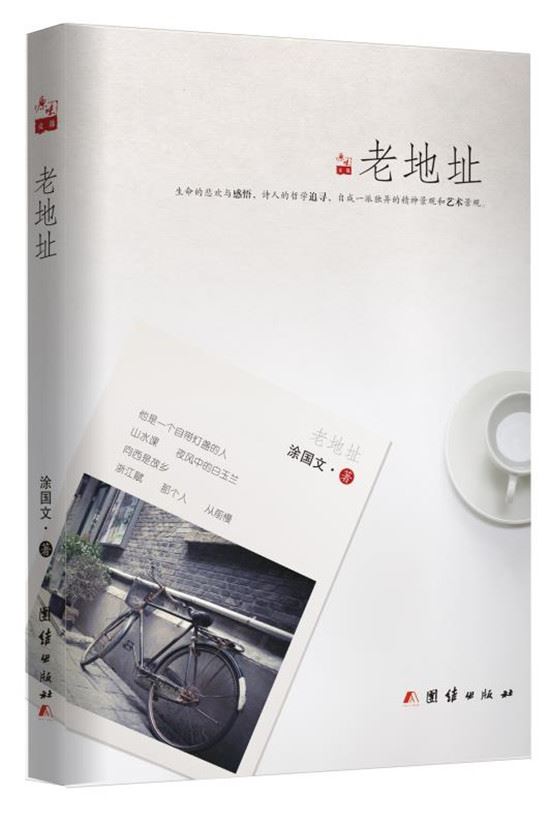
存在主义哲学对欧洲影响很大,但是任何哲学都无法和时间抗衡,“拯救”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哲学观念,还是生活概念,每个人程度不同地都需要拯救。对于哲学家来说, 对时间的解读是一个永恒的课题,对于诗人也是这样,作者在《时光屠夫》中,把“时光”与“屠夫”并列起来,本身就令人深省,况且,作者切入的角度比较特殊,用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时间对于生命的蚕食,更有特殊的意义。诗歌《惊鸟》不满足于对于事物的表面解读,而是深入事物的本质,对于人性的异化进行揭露,“人是一种最危险的动物/人的味道,是一种最难闻的气味”。这当然是对异化之后的人性来讲的,人活在物质世界不可能不被异化,只有那少数不断与自我劣性进行斗争的人,才可能实现道德完善。
诗歌用怎样的表达方式去写,是诗人自己的事情,而诗人作品的气场和存在价值,却和一个诗人的造化有关:内在的、外界的、地域的、世界的、单纯的、复杂的……对于任何作家来说,“怎样写”要比“写什么”更加重要,对于诗人来说也是这样,诗人内在素质常常表现在对生活素材的观察与表现上,如诗歌《半歌》对“半”字有自己独到的思考,无论是人生还是事业,很多时候,“半”比完整更好。再如作者在《刀的发生学》别出心裁地用“发生学”角度,用整体的氛围去烘托刀的复杂性,无论是石头的滚动,还是洪水的呼啸;无论是满天星光,还是对一台打磨机的打量,最终都把审美的触角凝聚到——刀。“刀”在这个文本中既是原因,更是结果,其内在关联令人深思。再比如诗歌《荒原》,作者把笔墨没有放在自然荒原,而是借代到文字的荒原,无论是小说的涌动,还是散文的挺拔;无论是格言的犀利,还是成语的慵懒,一起汇合成文字的原生态之河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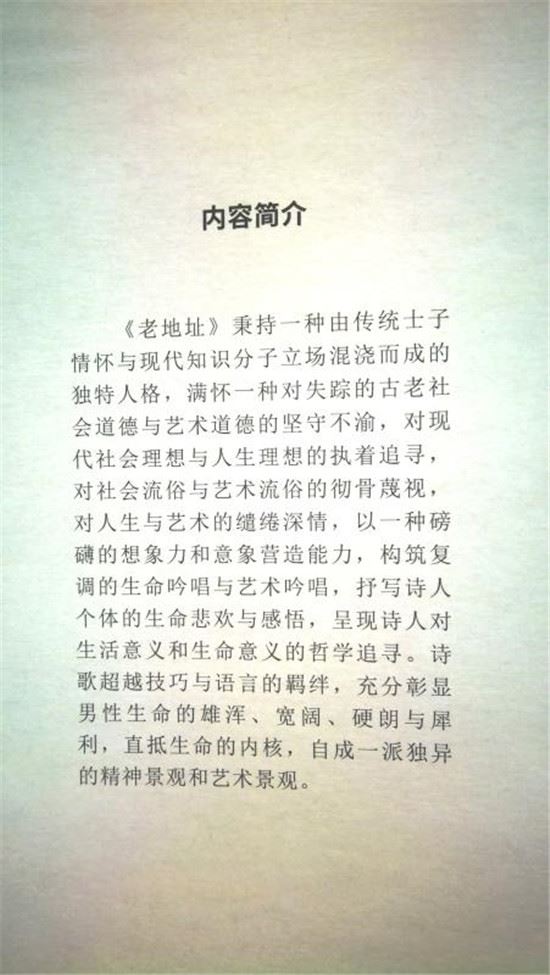
诗歌是最简练、最精粹的文字,是文字的最高形式。目前中国白话诗到底在哪一个阶段?很多人并不清晰。在笔者看来,中国当代诗歌经历了四个阶段:第一个阶段是向外学习;第二个阶段是对内寻找,即是文化寻根;第三个阶段是向下挖掘;第四个阶段是向上超越。诗歌是需要有气场的。一首诗歌的气场大小来自于对生活深度的挖掘,涂国文的《神灯》是诗歌,更呈现了做人的标杆,一位诗人需要“点燃自己,照耀自己”,更需要把灯盏成为“自己的神灯”,这就无形中打开了诗歌的宗教的门。任何有作为的诗人,总是自觉地与大师相遇,涂国文在《楼道上的卡夫卡》中就与世界一流的小说家卡夫卡“相遇”,看见小说大师卡夫卡“被卡在了布拉格某栋楼层楼道”,文本中的“看见”其实是一种幻象,诗歌写作很多时候用幻象而不用实景,反而更加强化了生活的本质。诗歌《仰望》凸显了精神高度,“精神”高到怎样的程度呢?那就是要讴歌善良,讴歌劳作,讴歌山川和谐,讴歌人类与其他动植物同在,讴歌自由……没有这些讴歌,就没有生命的正能量。
诗歌的深度是重要的,广度更加重要。有些人写诗是写给某一个朋友的,有的则是写给自己情人的,就免不了在语气上窃窃私语,气场不足。涂国文写作诗歌气场很宽阔——与整个世界进行对话。他在《我有许多诗篇是写给这世界》中直接表达了自己的人生信条,那就是“不平庸”,努力把自己的内在之光投影在世界。当然,涂国文诗歌并不总是张扬的,也有很内敛的时候,他在诗歌《乌岩头村之夜》写作就显得非常内敛,“我暂时还不准备将黑夜交出/我想积攒它/练出我生命中的乌金”。涂国文还在《灯塔》中对于海盗的职业进行了重新诠释,摒弃了海盗谋财害命的公式化恶行,把海盗与灯塔相联系,“偷来各式灯塔,它是我的罪证/也是我向往光明的证词。”这样,传统意义上的“海盗”就有了新的意义。
在这本诗集中,涂国文除了直抵本质外,还对祖国山河进行了审美观照。他写祖国山河之美並没有满足于对山河外在美的描写,而是在努力提炼一种“美的精神”,努力提炼风景之后的别异的美,使“美”成为心灵的一部分,如诗歌《向西是故乡》,“西”本来是一个地理概念,在作者文本中却成了美学概念,“月光千里,代替故乡流照异乡/代替游子抚摸触故乡”。作者还在《涂家村81号》《乡情庭院》《我对鄱阳湖的爱比你们要深三重》表达了同样的风景审美升华。

图为涂国文。
涂国文不仅努力观察万事万物,还对诗坛本身有浓厚的兴趣,他在《诗坛》中既有对诗坛乱象的分析,更有对诗歌“烈士”品质的颂扬。作者在《写怎样的诗》中这样叙述“写远离修辞却贴近灵魂,被庙堂之事搅乱/却在江湖之远口口相传的诗”。在涂国文的修辞学中,把“青衣”比作动词,把“小生”比作名词,就非常新颖,而且有陌生感。作者还借助于词类学对“桥”进行审美观照:桥洞下的水流如动词,桥身上镶嵌着名词和代词,而介词如同楔石……这些词类“将生存与生活融通”,具有强烈的反讽效果。
诗歌写作是相对稳定的,由每个时代对于她进行补充,不可能每个时代把诗歌历史放到一边,自己重打锣鼓另开张。对于诗人来说,只有感知透了诗歌历史,才不至于走到窄巷,涂国文就是具有这样高度责任性的诗人,他在诗集第五辑《雕像》中,自觉地对外国伟大诗人进行解读,用精神去感知精神,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,其中有对米沃什的解读,有对策兰的怀念,有对赫尔博斯的理解……这些精美的诗歌图画不仅仅是对伟大诗人成就的展示,更反映了诗人本人对于诗歌历史的深刻理解。
涂国文住在南方,笔者住在北方,虽然居住环境风格不同,但是对于诗歌精神的理解基本相同,在这篇并不算深刻的评论文章里,笔者与作者共同经历了精神冒险,也共同得到了审美幸福。在此,谨祝涂国文在诗歌的宽度和深度方面继续攀登,写出更精美的作品,给读者带来更多惊喜。
2021年3月于青城
版权及免责声明: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,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“英国富中传媒”,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。凡转载文章,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。版权事宜请联系:619378122@qq.com。